[摘要]《懸崖之上》是一部值得從電影制作的不同維度展開(kāi)多元化討論的佳作,對(duì)視覺(jué)呈現(xiàn)與影像表達(dá)的分析,更是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整體而言,在《懸崖之上》的攝影創(chuàng)作中,攝影指導(dǎo)趙小丁攻克了“雪一直下”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建構(gòu)了“以小見(jiàn)大”的深刻表達(dá),踐行了影像技術(shù)的新探索,依靠獨(dú)具匠心的藝術(shù)思維與難能可貴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有效地助推了一部高品質(zhì)諜戰(zhàn)片的精彩呈現(xià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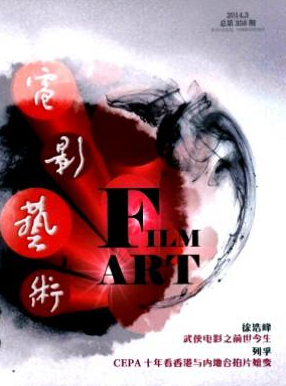
本文源自程檣, 電影藝術(shù)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6-22
[關(guān)鍵詞]《懸崖之上》趙小丁諜戰(zhàn)片雪的拍攝攝影技術(shù)探索
在張藝謀看來(lái),由他執(zhí)導(dǎo)的諜戰(zhàn)題材電影《懸崖之上》最為核心的創(chuàng)作主題是聚焦、展現(xiàn)和歌頌隱秘陣線上的無(wú)名英雄及其家國(guó)情懷。整體而言,《懸崖之上》有效地縫合了傳統(tǒng)主旋律電影在“叫好”與“叫座”之間的錯(cuò)位或撕裂,以類型化生產(chǎn)的諜戰(zhàn)片樣態(tài)實(shí)現(xiàn)了思想、藝術(shù)、制作各層面的提升和有機(jī)統(tǒng)一,也在市場(chǎng)層面拓寬了新主流電影的創(chuàng)作格局,是一部典型的講中國(guó)故事、傳中國(guó)聲音的高品質(zhì)商業(yè)片。關(guān)于《懸崖之上》的討論,可以從多個(gè)維度細(xì)致展開(kāi),但視覺(jué)呈現(xiàn)與影像表達(dá)作為文本表征與敘事風(fēng)格最為基礎(chǔ)、最為直觀的展示,顯然是不可回避的重點(diǎn)。如《懸崖之上》的攝影指導(dǎo)趙小丁所言,影像與故事內(nèi)容關(guān)系緊密,并建構(gòu)起一系列具有連鎖反應(yīng)的影像元素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進(jìn)而生成了電影化敘事的基本輪廓。
戴著腳鐐跳舞:“雪一直下”的現(xiàn)實(shí)挑戰(zhàn)
張藝謀在電影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特別重視通過(guò)視覺(jué)造型手段去營(yíng)造敘事情境與敘事氛圍,其目的在于激發(fā)受眾的視知覺(jué)經(jīng)驗(yàn),以幫助他們更為直接地感受和理解影像故事的內(nèi)容表達(dá)。這是影像敘事與文字?jǐn)⑹碌闹匾獏^(qū)別,也是構(gòu)成電影生命力的關(guān)鍵要素。《懸崖之上》的敘事時(shí)間是冬天,敘事地點(diǎn)是20世紀(jì)30年代的哈爾濱。在這樣一個(gè)指向性十分鮮明的特定環(huán)境中,《懸崖之上》除最后一兩場(chǎng)戲以外,其他的室外場(chǎng)景全部都彌漫著紛飛的大雪,以及諸多室內(nèi)場(chǎng)景也能看到雪的“影子”,所以“雪一直下”隨之成為整部影片最為核心、最為重要的視覺(jué)符號(hào)。可以說(shuō),“雪一直下”不僅生成了凜冽的影像風(fēng)格與一種殘酷美學(xué)的詩(shī)意敘事,也與其他導(dǎo)演、其他國(guó)家的諜戰(zhàn)片在影像呈現(xiàn)上生成了鮮明的區(qū)別。
雪從何來(lái)?顯然是“雪一直下”的第一要義。也就是說(shuō),需要完成“雪一直下”的創(chuàng)作任務(wù),不僅需要善于利用真實(shí)的自然環(huán)境,更需要積極嘗試采取最新的環(huán)保技術(shù)去制造。經(jīng)過(guò)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的反復(fù)研究與多次確認(rèn)之后,《懸崖之上》在拍攝中重點(diǎn)用了兩種造雪方式。一種是韓國(guó)的造雪工藝,采用一種類似膨化食品的物質(zhì)去制造呈現(xiàn)小顆粒狀的假雪,它的質(zhì)感和重量特別像漂浮空中的真雪,而且材料對(duì)環(huán)境沒(méi)有任何污染。還有一種方式就是利用滑雪場(chǎng)的造雪機(jī)。除少量真雪之外,鏡頭中的雪大多采用了這兩種技術(shù)制造的假雪,而縱深場(chǎng)景里的雪也會(huì)依靠電腦完成后期制作去進(jìn)行延伸。這一處理方式同時(shí)涉及光線的調(diào)整、鏡頭角度的選擇及焦距的把控等攝影技術(shù)層面的重點(diǎn)與難點(diǎn),也給趙小丁的創(chuàng)作提出了新挑戰(zhàn)與新要求。
從最終的視覺(jué)效果來(lái)看,《懸崖之上》里的“雪”不是平面、孤立的,而是有層次、有縱深的,在塑造人物、表達(dá)主題、營(yíng)造情境、烘托氣氛等層面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關(guān)鍵作用。趙小丁還回憶到,在拍攝《影》的時(shí)候,導(dǎo)演張藝謀希望營(yíng)造“雨一直下”的視覺(jué)效果,所以現(xiàn)場(chǎng)拍攝時(shí)安裝了很多“下雨”的裝備,趙小丁根據(jù)自己對(duì)畫(huà)面的反復(fù)測(cè)試,決定在一些管子上面打孔,孔徑有大有小,然后再給水加壓,最終達(dá)到了預(yù)期效果。趙小丁感概,“下雨”和“下雪”其實(shí)都挺有技術(shù)含量的,體現(xiàn)著一絲不茍與細(xì)致嚴(yán)謹(jǐn)?shù)墓そ尘瘛Zw小丁也笑稱,拍《一秒鐘》的沙塵暴畫(huà)面全靠運(yùn)氣好,因?yàn)檎泌s上了沙塵暴,所以呈現(xiàn)出來(lái)的影像效果是實(shí)拍完成的。
為了真實(shí)客觀地塑造“雪一直下”的視覺(jué)表征與影像質(zhì)感,《懸崖之上》的很多拍攝工作都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溫環(huán)境中完成的。在這樣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下進(jìn)行拍攝,需要提前進(jìn)行反復(fù)測(cè)試,厘清相應(yīng)的解決措施,以保障數(shù)字?jǐn)z影機(jī)在低溫環(huán)境下保持正常的工作狀態(tài)。此外,在溫差顯著的拍攝環(huán)境中,鏡頭鏡片也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霧和霜,有時(shí)候還不是在第一片透鏡或者最后一片透鏡,而是在中間的透鏡上,這就非常麻煩,因?yàn)檫@個(gè)位置的霧氣一時(shí)半會(huì)兒還消退不下去。所以《懸崖之上》的整個(gè)攝影組在鏡頭數(shù)量的配備上遠(yuǎn)超以往的任何一次創(chuàng)作,唯有如此,才能以備隨時(shí)調(diào)換,確保正常的拍攝進(jìn)度。趙小丁還提到,在東北和大同的實(shí)際拍攝過(guò)程中,由于室外溫度多在零下30多度、室內(nèi)溫度則在零上20多度,每天出發(fā)前和收工時(shí)為了讓鏡頭和攝影機(jī)盡量避免巨大溫差,存放器材的房間基本不開(kāi)暖氣,以便讓器材處于零度左右的室溫,保證拍攝現(xiàn)場(chǎng)的順利進(jìn)行,收工時(shí)要先把器材放到酒店前廳,讓它一點(diǎn)點(diǎn)適應(yīng)溫差。顯然,“雪一直下”的藝術(shù)追求與低溫拍攝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也給《懸崖之上》的攝影創(chuàng)作在人力層面增添了諸多消耗。
趙小丁認(rèn)為,攝影創(chuàng)作需要很自然地貼合故事的造型傾向,故事情境是統(tǒng)領(lǐng)攝影調(diào)性的主引擎。“雪一直下”的鏡頭表達(dá)首先是一種大自然的客觀現(xiàn)象,其實(shí)代表了寒冷與殘酷,正應(yīng)和了影片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懸崖之上》的故事情境決定了“雪一直下”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所以他們并沒(méi)有為了單純營(yíng)造視覺(jué)美而刻意為之,而是盡最大的努力去真實(shí)地還原敘事所需的視覺(jué)元素與影像質(zhì)感。他還提到在拍《一秒鐘》的沙漠場(chǎng)景時(shí),有意識(shí)地回避了為美而美的影像呈現(xiàn)方式。不論是下雪,或者是沙漠,努力呈現(xiàn)自然環(huán)境的真實(shí)之美,而不是追求懸浮、奇觀的夸張表達(dá),這體現(xiàn)了攝影創(chuàng)作的價(jià)值訴求與藝術(shù)自覺(jué)。
使用過(guò)膠片的攝影師通常會(huì)有一個(gè)相似的感受,即下雪的時(shí)候特別容易曝光不足。因?yàn)檫^(guò)去都是用測(cè)光表量光,如果按照中性灰進(jìn)行曝光,雪拍出來(lái)一定是臟的。所以拍雪需要有充分的曝光,才能讓雪景達(dá)到最好的呈現(xiàn)。但是曝光過(guò)了就是一片白,無(wú)法展現(xiàn)出雪的肌理和質(zhì)感,會(huì)嚴(yán)重侵害應(yīng)有的真實(shí)性與審美性。趙小丁說(shuō),他是從膠片時(shí)代走過(guò)來(lái)的攝影師,那時(shí)候用的都叫感光材料;在北京電影學(xué)院讀書(shū)時(shí),有一門(mén)專業(yè)課主要教授的就是膠片感光曲線的應(yīng)用;作為攝影師,必須考慮各種拍攝物的反光率,以及在什么樣的曝光值下它的最終呈現(xiàn)是最準(zhǔn)確的。可以說(shuō),這些專業(yè)訓(xùn)練所奠定的影像觀念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是趙小丁不可或缺的創(chuàng)作素養(yǎng)與知識(shí)儲(chǔ)備。趙小丁認(rèn)為,數(shù)字?jǐn)z影機(jī)的設(shè)計(jì)理念全是源自于對(duì)膠片感光曲線的應(yīng)用,它的感光元件設(shè)計(jì)理念也是這么考慮的,現(xiàn)在主流使用的數(shù)字?jǐn)z影機(jī)性能都非常好,基本都具備14檔以上的光圈,有很好的寬容度和很高的靈敏度,所以通常只要在曝光掌握上沒(méi)有特別大的閃失,加上強(qiáng)大的后期流程作保證,在技術(shù)上的還原和呈現(xiàn)就不會(huì)出現(xiàn)太大差錯(cuò)。可以說(shuō),長(zhǎng)期積累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與迭代更新的數(shù)字技術(shù)為“雪一直下”的影像實(shí)踐奠定了“雙保險(xiǎn)”。
毫無(wú)疑問(wèn),藝術(shù)創(chuàng)新的另一面從來(lái)都是披荊斬棘,看似十分簡(jiǎn)單的“雪一直下”其實(shí)需要耗費(fèi)創(chuàng)作者巨大的精力去營(yíng)造才能達(dá)成預(yù)期的審美效果。在趙小丁看來(lái),雖然在《懸崖之上》的拍攝階段因?yàn)楦鞣N原因而遇到了重重困難,但是整個(gè)團(tuán)隊(duì)始終堅(jiān)持積極找尋解決方案、努力層層攻破難關(guān),不僅取得了最終的理想結(jié)果,也在過(guò)程中積攢了寶貴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獲得了探索影像創(chuàng)新的幸福感。
重視細(xì)節(jié)之美:“以小見(jiàn)大”的深刻表達(dá)
建構(gòu)宏大敘事,是主旋律電影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與敘事范式。與之相較,新主流電影的一個(gè)關(guān)鍵轉(zhuǎn)折與重要變化無(wú)疑是偏向微末敘事,巧用“以小見(jiàn)大”的修辭方式去形塑集體價(jià)值、傳達(dá)家國(guó)情懷,《我和我的祖國(guó)》《我和我的家鄉(xiāng)》等力作是這一轉(zhuǎn)型趨勢(shì)的典型詮釋。《懸崖之上》選擇歌頌無(wú)名英雄的創(chuàng)作初衷與新主流電影“以小見(jiàn)大”的常態(tài)化發(fā)展趨勢(shì)一脈相承。對(duì)趙小丁而言,如何通過(guò)影像元素去完成《懸崖之上》的“以小見(jiàn)大”是他必須解決的創(chuàng)作議題,他也認(rèn)為保持敏感心態(tài)、重視細(xì)節(jié)之美是行之有效的表達(dá)策略。需要指出的是,敏感是一種特殊的心理活動(dòng),在攝影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為攝影師如何展開(kāi)具體創(chuàng)作,而不是探究為何創(chuàng)作,在某種意義上指向了充滿迷思的藝術(shù)靈感。
對(duì)影像色彩的搭配與處理,既需要從宏觀層面去把握影片的思想主旨與視覺(jué)風(fēng)格,也需要從微觀層面去契合每一個(gè)場(chǎng)景、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的具體表達(dá);既彰顯攝影師一以貫之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也蘊(yùn)含藝術(shù)實(shí)踐過(guò)程中難能可貴的靈光乍現(xiàn)。在趙小丁看來(lái),冷色調(diào)是《懸崖之上》的影像底色,黑、白是攝影主調(diào),其中,白色占據(jù)主色調(diào)。這是由影片的外部環(huán)境與故事內(nèi)部的真實(shí)環(huán)境共同決定的,同時(shí)也象征了地下黨的命運(yùn)。但是在凜冽與殘酷之外,《懸崖之上》真正想要傳達(dá)的是舍生取義的大情大愛(ài)及黑暗終將被黎明打破的歷史邏輯。所以在影像元素中加入一撇暖色,有意識(shí)地呈現(xiàn)出冷暖對(duì)比,不僅豐富了影片的細(xì)節(jié)之美,更體現(xiàn)創(chuàng)作者的匠心獨(dú)運(yùn)與藝術(shù)靈感。在趙小丁看來(lái),這種對(duì)比,不僅僅是白雪與鮮血的強(qiáng)烈沖突,更為重要的表達(dá)方式則是默默地在很多凜冽的場(chǎng)景中加入了一點(diǎn)兒不容易被觀眾察覺(jué)的暖色系燈光。這種悄無(wú)聲息的細(xì)節(jié)處理讓《懸崖之上》的視覺(jué)表征與影像敘事變得更為精致、更為飽滿、更為感人。趙小丁提到,就算是在日景條件下,他們也保留了室內(nèi)的燈光,讓暖色系的燈光能有一個(gè)較為明顯的呈現(xiàn),無(wú)論是書(shū)店,還是他們二組居住的那個(gè)廢棄洋樓,包括高彬所在的警察局和辦公室等場(chǎng)景,都采用了這種方式方法,就是為了在寒冷環(huán)境下形成一種鮮明對(duì)比、塑造一種內(nèi)在沖突,同時(shí)建構(gòu)和傳達(dá)一種信念、一種希望。趙小丁特意強(qiáng)調(diào)了這種表達(dá)方式是他們有意為之。關(guān)于這一細(xì)節(jié)設(shè)計(jì)的處理,導(dǎo)演張藝謀在接受《電影藝術(shù)》雜志采訪時(shí),如是肯定:“我們常常用寒夜中的燈光這一暖色去點(diǎn)綴,讓它看上去似乎永遠(yuǎn)是人們心目中那個(gè)柔軟的地方,好像是你的家,是一個(gè)歸屬。所以在影片當(dāng)中,在所有的寒夜之中,漫漫長(zhǎng)夜中,常常會(huì)有一些暖色的燈光在這里去調(diào)節(jié),也是影片所寄托的另一層含義——他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情感。這樣暖色的燈光在電影里邊的點(diǎn)綴,與黑白形成了顏色反差,讓影片的影調(diào)更為立體和豐富。”
“雪一直下”的視覺(jué)呈現(xiàn)基本貫穿了影片的敘事始末,但是在拍攝影片最后幾個(gè)場(chǎng)景時(shí),趙小丁明確提出了別再“下雪”的建議,也得到了導(dǎo)演張藝謀的肯定。趙小丁的這一靈感可被視為《懸崖之上》整體影像表達(dá)的畫(huà)龍點(diǎn)睛之筆,雖然積雪很厚,但是天空中卻不再飄雪了,預(yù)示著“黎明”快要到來(lái)了,也完美地契合了周乙對(duì)小蘭說(shuō)的那句“你要活著看到黎明”的寄語(yǔ)。趙小丁也談道,在為數(shù)不多的幾場(chǎng)“雪不再下”的戲里,人物都有著美好的、溫暖的輪廓光,恰好拍攝時(shí)天氣不錯(cuò),就利用了自然光完成了相關(guān)鏡頭的拍攝。還有結(jié)尾的那場(chǎng)戲,也十分值得玩味,同樣是雪過(guò)天晴的場(chǎng)景,王郁靜靜地佇立在雪地,穿著大棉襖、揣著手,人物形象從勇敢無(wú)畏的地下黨轉(zhuǎn)化成了等待子女歸來(lái)的平凡母親,因此鏡頭里的畫(huà)面處理必須特別質(zhì)樸、特別簡(jiǎn)單。雖然雪已經(jīng)停了,但當(dāng)攝影機(jī)推近去拍她眉毛上的冰霜時(shí),我們自然就知道她已經(jīng)在雪地中等待了許久,她等待的既是失散多年的一雙兒女,也是革命事業(yè)的勝利。可以說(shuō),趙小丁“不再下雪”的細(xì)節(jié)設(shè)計(jì)既源于藝術(shù)靈感的滋養(yǎng),也體現(xiàn)著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與生活體驗(yàn)的沉淀,也正是這樣巧妙的處理,讓《懸崖之上》的影像表達(dá)更有敘事層次、更具審美意味。
《懸崖之上》里的火車,是在北京的攝影棚里搭出來(lái)的三節(jié)車廂。趙小丁在這三節(jié)車廂的兩邊都加了相應(yīng)數(shù)量的燈,也對(duì)這些燈進(jìn)行了一些采樣和編程做成燈帶,以便讓光流動(dòng)起來(lái)。在以往的電影攝影中,很少有這么大面積地用電子編程的方式去做火車車廂燈光的實(shí)踐。車廂雖然實(shí)際上是靜止的,但是通過(guò)光影變化,可以讓它看上去處于運(yùn)動(dòng)之中。這是因?yàn)榫拔锘瑒?dòng)時(shí)會(huì)有光影變化,這光影變化不只有明暗,還有光的流動(dòng)。此外,道具組也對(duì)這三節(jié)車廂做了一些機(jī)械裝置,使火車車廂的連接處可以實(shí)現(xiàn)不同程度的扭動(dòng)。這樣一來(lái),兩側(cè)的燈帶結(jié)合車身的晃動(dòng)模擬,就可以建構(gòu)出火車行駛的運(yùn)動(dòng)狀態(tài)。當(dāng)然,單純讓火車動(dòng)起來(lái)是不夠的,還要讓車窗外的景物也真實(shí)地存在、真實(shí)地流轉(zhuǎn),才能讓火車戲“活起來(lái)”。所以觀眾能看到的那些車窗外的樹(shù)木、雪景等視覺(jué)環(huán)境,都是經(jīng)趙小丁前期嚴(yán)格測(cè)算光孔與焦距后,去東北實(shí)際拍攝回來(lái)的素材,再經(jīng)由特效處理,就可以完完全全地“以假代真”了。可以說(shuō),對(duì)火車細(xì)節(jié)呈現(xiàn)的精益求精,讓《懸崖之上》的相關(guān)鏡頭彰顯出了極致的視覺(jué)之真與影像之美。
動(dòng)作戲的設(shè)計(jì)團(tuán)隊(duì)來(lái)自韓國(guó),曾參與制作過(guò)《太極旗飄揚(yáng)》等影片。韓國(guó)團(tuán)隊(duì)的創(chuàng)作特長(zhǎng)是寫(xiě)實(shí)風(fēng)格,但因?yàn)榭催^(guò)《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俠電影,所以設(shè)計(jì)了一系列酷炫的動(dòng)作戲。這種設(shè)計(jì)恰好與《懸崖之上》求真求實(shí)的審美質(zhì)感有悖,也和張藝謀的導(dǎo)演創(chuàng)作思路相反,后期剪輯因此刪掉了所有存在“套路感”的動(dòng)作鏡頭,讓影像表達(dá)重回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觀念。此外,飆車戲是動(dòng)作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懸崖之上》的攝影難點(diǎn)之一。趙小丁坦言,拍這些老爺車在雪地上追車、飆車的戲,花費(fèi)了相當(dāng)多的工夫和時(shí)間,尤其是對(duì)光的設(shè)計(jì),必須特別嚴(yán)謹(jǐn)和考究。為了讓車的造型更符合歷史質(zhì)感,道具組借用了多輛愛(ài)好者收藏的老爺車,但是它們的動(dòng)力系統(tǒng)年久失修,因此在拍攝過(guò)程中需要做出很多設(shè)計(jì)和調(diào)整才能實(shí)現(xiàn)理想的視覺(jué)效果。街道場(chǎng)景等夜戲,基本上都是利用路燈和這些老爺車的車燈進(jìn)行照明處理,車燈基本上按照當(dāng)時(shí)老車輛的現(xiàn)實(shí)狀況進(jìn)行還原,而且有一些人物的戲直接就是用這些車燈作為逆光光源。比如,王郁的車和特務(wù)的車相撞之后的背景,就是利用特務(wù)車輛的大燈打開(kāi)之后營(yíng)造的逆光氛圍。顯然,不論是對(duì)動(dòng)作設(shè)計(jì)的刪繁就簡(jiǎn),還是對(duì)飆車場(chǎng)景的用心勾勒,都是為了利用好每一個(gè)細(xì)小的視覺(jué)元素,讓觀眾更好地沉浸于《懸崖之上》的影像世界,跟隨鏡頭去感受故事的跌宕起伏與驚心動(dòng)魄。
堅(jiān)持與時(shí)俱進(jìn):努力創(chuàng)新的技術(shù)探索
在某種意義上,技術(shù)的更新迭代會(huì)直接作用于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觀念,激發(fā)出全新的表達(dá)形式,尤其對(duì)攝影創(chuàng)作而言,技術(shù)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作為職業(yè)攝影師,趙小丁對(duì)新技術(shù)的態(tài)度始終保持理性與客觀。在數(shù)字技術(shù)持續(xù)進(jìn)化的過(guò)程中,趙小丁的攝影觀是在創(chuàng)作中發(fā)揚(yáng)優(yōu)良傳統(tǒng)、堅(jiān)持寶貴經(jīng)驗(yàn)、明確價(jià)值導(dǎo)向,在創(chuàng)作中善用最新技術(shù)、優(yōu)化影像表達(dá)、追求時(shí)代氣息。
以什么樣的心態(tài)面對(duì)技術(shù),始終是攝影師不可回避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在趙小丁看來(lái),當(dāng)下大部分?jǐn)z影師因此分成了兩個(gè)截然不同的極端,有些人對(duì)新技術(shù)的接受比較慢,或者排斥新技術(shù),很容易就會(huì)遭遇職業(yè)困境,也有像羅杰·狄金斯這樣始終對(duì)新技術(shù)飽含熱情、保持跟進(jìn)的攝影師。數(shù)字技術(shù)時(shí)代,很多電影鏡頭都是在電腦環(huán)境中完成的,但是如何打光、如何選鏡頭角度、怎么下鏡頭、怎么選鏡頭焦距等攝影問(wèn)題與實(shí)拍的要求其實(shí)是一致的,只是場(chǎng)景變成了虛擬的,但依然需要攝影師的深度參與。趙小丁認(rèn)為,攝影師必須要敞開(kāi)懷抱去接納新技術(shù)環(huán)境、去掌握新技術(shù)創(chuàng)作;與此同時(shí),技術(shù)進(jìn)步促使后期前置,也在某種層面上大幅提升了攝影師的話語(yǔ)權(quán)。
談及《懸崖之上》的技術(shù)運(yùn)用時(shí),趙小丁重點(diǎn)提到了開(kāi)場(chǎng)跳傘戲的主觀鏡頭。在正式開(kāi)拍之前,他們做了大量的測(cè)試,基本操作思路是先用小型航拍機(jī),用關(guān)閉引擎的方法讓它幾乎變成一種自由落體,最后落到地上,獲得了垂直向下的主觀鏡頭;還有一些像GoPro、Action這樣的小設(shè)備,會(huì)把它放在紙箱里面,并在紙箱的側(cè)面挖個(gè)孔,使鏡頭沖著側(cè)面,這樣影片中才有了一些下落過(guò)程中側(cè)面角度;然后,用無(wú)人機(jī)的機(jī)械手把紙箱掛在上面,飛上天之后再放開(kāi),那個(gè)小攝影機(jī)就會(huì)在空中實(shí)現(xiàn)自由落體。為了讓這一場(chǎng)跳傘戲的主觀視角足夠逼真,趙小丁拍了很多角度,有些鏡頭落到樹(shù)梢時(shí)甚至還有一些撞擊感,還有便是從地面升起無(wú)人機(jī),然后倒放。最后導(dǎo)演張藝謀從里邊剪出了一部分視覺(jué)感受極具沖擊力的鏡頭,有效地完成了影片開(kāi)場(chǎng)氛圍的視聽(tīng)營(yíng)造。
趙小丁也以《地心引力》和《人猿泰山》為例,講述了技術(shù)進(jìn)步對(duì)攝影師的重要性。與視效公司做預(yù)覽,是《地心引力》前期籌備的工作重中之重,其比例接近于未來(lái)完成的90%,因此,實(shí)際開(kāi)機(jī)后的拍攝效率得以大幅提升、拍攝周期切實(shí)縮短。趙小丁曾仔細(xì)研讀過(guò)《人猿泰山》的拍攝技術(shù)報(bào)告。《人猿泰山》前期籌備時(shí),劇組專門(mén)做出了一個(gè)陀螺儀的航拍矩陣,具體是用6臺(tái)RED,3臺(tái)在上、3臺(tái)在下,組合成一個(gè)36,000多K的高清晰度拍攝,在東非大草原用多架直升機(jī)記錄了大量的有效素材,包括原始森林最美的黃昏時(shí)刻,回來(lái)以后迅速把素材建成完全仿真的場(chǎng)景。《人猿泰山》的很多場(chǎng)景都是在棚內(nèi)完成的,本來(lái)非洲最有魅力的光可能每天只能出現(xiàn)15分鐘,但在技術(shù)加持下,劇組可以在棚里用所需的光線完成全天侯的拍攝。毫無(wú)疑問(wèn),有了這種技術(shù)和能力以后,整個(gè)電影工業(yè)生產(chǎn)的流程都會(huì)發(fā)生質(zhì)的改變。趙小丁也深深地感慨,沒(méi)掌握新技術(shù)的攝影師很快就會(huì)沒(méi)活干了,這就是新技術(shù)對(duì)每個(gè)從業(yè)人員而言的重要性。
在電影工業(yè)化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下,拍攝周期的長(zhǎng)短與資本投入的多少直接掛鉤,高概念商業(yè)大片的生產(chǎn)有兩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即保證高品質(zhì)與追求高效率。《懸崖之上》一共拍攝了88個(gè)工作日。在雪鄉(xiāng)拍了20多個(gè)工作日,在牡丹江小火車站大概拍了10個(gè)工作日,在大同的棚里拍了小一個(gè)月,最后回到北京。趙小丁配備一組4臺(tái)攝影機(jī),要是分AB兩組,B組是2到3臺(tái),雖然期間經(jīng)歷了新冠肺炎疫情最嚴(yán)重的時(shí)刻,劇組停工了兩個(gè)多月,但是88天的高效率完成度與趙小丁對(duì)新技術(shù)的熟練運(yùn)用和電影工業(yè)化流程的長(zhǎng)期探索密不可分。
技術(shù)進(jìn)步給攝影師帶來(lái)了多元利好,既全方位豐富了影像表達(dá)的想象力,也進(jìn)一步解放了攝影創(chuàng)作的生產(chǎn)力,有助于攝影師更專注于對(duì)故事本身的考察與表達(dá)。趙小丁提到,現(xiàn)在的后期色彩管理系統(tǒng)完成不同機(jī)器調(diào)色的技術(shù)已變得非常強(qiáng)大,以及主流廠商生產(chǎn)的數(shù)字?jǐn)z影機(jī)的綜合技術(shù)指標(biāo)都比較接近,所以在選擇攝影機(jī)型號(hào)及鏡頭時(shí),無(wú)須再保守地考慮色調(diào)表現(xiàn),而且在直接成像技術(shù)的作用下,這些擔(dān)心在后期都可以輕易地解決。所以面對(duì)《懸崖之上》的拍攝,趙小丁對(duì)攝影機(jī)的選擇重點(diǎn)考察的是重量、體積、寬容度、色域、空間和感光度等層面的細(xì)微差異,出發(fā)點(diǎn)是更好地服務(wù)于“心向黎明、舍生忘死”的故事主題與諜戰(zhàn)片的類型質(zhì)感。
技術(shù)的進(jìn)步以及對(duì)技術(shù)的接受,從來(lái)都不會(huì)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個(gè)循序漸進(jìn)的過(guò)程。趙小丁也十分同意這一觀點(diǎn)。他認(rèn)為,電影其實(shí)沒(méi)有一個(gè)特定的標(biāo)簽,就好像變形寬銀幕鏡頭能夠形成一種特殊的景深觀感,很多人就把這種視覺(jué)感受記錄下來(lái),成為了一種視覺(jué)記憶,認(rèn)為這就是寬銀幕電影的影像特征,但這種技術(shù)其實(shí)只是在三四十年前因?yàn)樾枰淖儺?huà)幅構(gòu)圖比例才出現(xiàn)的,但這個(gè)技術(shù)也使畫(huà)面損失了很多的影像。所以技術(shù)改變的另一面是觀念與習(xí)慣的改變,就好像現(xiàn)在如果給新一代的攝影師看那些動(dòng)態(tài)模糊的影像,反而會(huì)讓他們覺(jué)得很不習(xí)慣、很不喜歡。事實(shí)上,縱覽趙小丁的攝影創(chuàng)作之路,不難發(fā)現(xiàn),他始終在堅(jiān)持與新技術(shù)對(duì)話、用新技術(shù)表達(dá),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夠不斷創(chuàng)造出精品影像內(nèi)容的重要策略。
技術(shù)與情感,往往是理性與感性的另一種說(shuō)辭,看似是對(duì)立關(guān)系,實(shí)則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在討論技術(shù)之余,趙小丁也提到了自己對(duì)這一觀點(diǎn)的看法。從電影的發(fā)展史來(lái)看,電影離不開(kāi)技術(shù),從默片到有聲片、從黑白到彩色、從膠片到數(shù)字,技術(shù)變革決定了電影創(chuàng)作的每一個(gè)關(guān)鍵時(shí)刻,這是電影工業(yè)化發(fā)展的歷史必然。但哪怕像科幻片這樣帶有強(qiáng)技術(shù)屬性、強(qiáng)工業(yè)屬性的電影,依然需要認(rèn)真地探究如何表達(dá)才能與時(shí)代、與受眾實(shí)現(xiàn)共情。技術(shù)的層出不窮會(huì)讓電影創(chuàng)作產(chǎn)生本質(zhì)上的變革,但這并不代表“唯技術(shù)論”,更不代表對(duì)“情感”的漠視。技術(shù)與情感為電影創(chuàng)作提供了不同的參照,但情感是電影的內(nèi)核、技術(shù)是電影的外延,二者的和諧共融才是電影創(chuàng)作持續(xù)向前的主引擎。《懸崖之上》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是為了更好地服務(wù)于影片情感的傳達(dá),讓受眾能夠更深入與人物共情、與故事共情,因?yàn)閷?duì)于廣大的普通觀眾而言,他們關(guān)注的核心并不是技術(shù)如何實(shí)現(xiàn)登峰造極,而是電影本身的情感內(nèi)核夠不夠真摯可信、夠不夠感人肺腑。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jiàn)問(wèn)題 >
SCI常見(jiàn)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