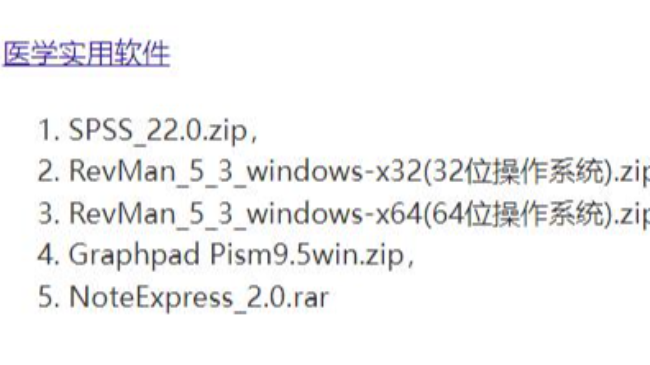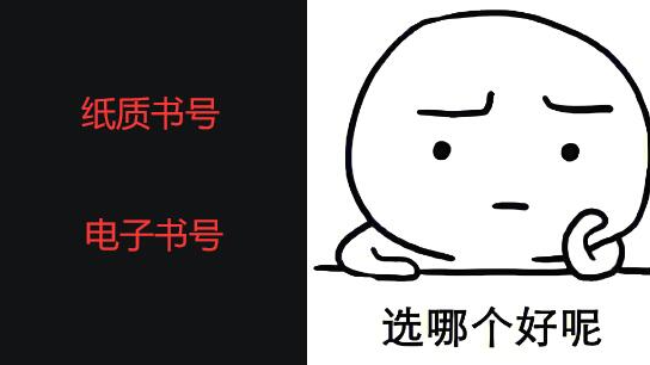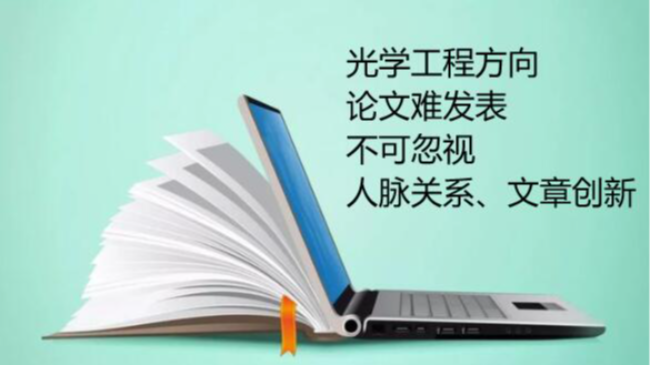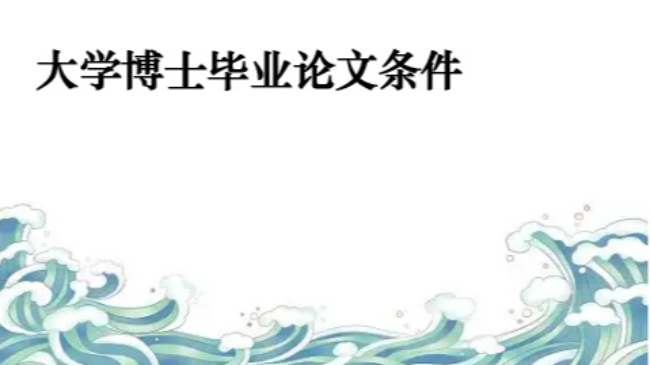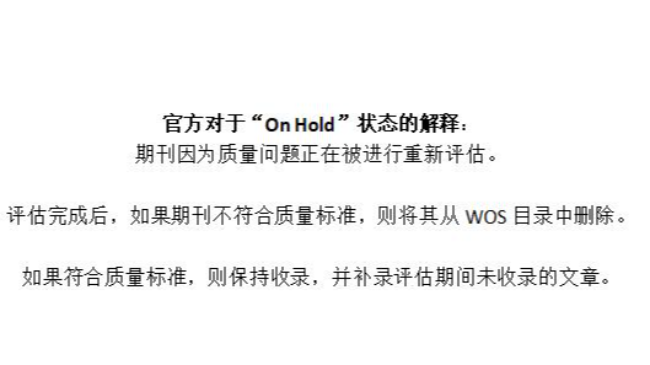藝術語言論文:紀錄片中語言的真實性解析
本文作者:劉峰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
由于歷史事件已經成為過去式,不具備拍攝真實環境與時間中的人物與事件的條件,即便是有歷史遺址、遺跡、文物等,但它們都是靜態的而且需要精心保護,所以就難以獲得生動的可視性材料,這使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成為一項艱難的藝術勞動。
為了解決可視性材料缺乏的難題,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者們進行了大量的探索,通過各種手段去彌補創作中的不足,其中最常見的有當事人講述、專家采訪、真實再現等。當事人講述是由當事人口述記憶中的歷史事件,或呈現其日記、文字材料、圖片等輔助性材料,專家采訪是由歷史學者、專家講述歷史事件,引導觀眾從專業學術角度認識歷史,這兩種方法可以彌補史料不足,但仍沒有提供與歷史事件直接相關的可視性材料。真實再現解決了這一問題,它采用搭景搬演的方式,通過寫實或寫意的歷史場景搭造以及演員表演再現歷史情景。三種表現手法運用中如果把握不好尺度,便會違背真實性原則,因為三者都不是直接拍攝的現場影像,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主觀的成分。真實性是不可違背的原則,否則就不能稱其為紀錄片,不過由于題材限制使得以上三種手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一定爭議,尤其以真實再現最為集中,但只要堅持歷史真實性原則的底線,不為了單純追求影像質量而進行虛構和造假,都能得到廣泛的認可。
近年來,動畫藝術語言由于在重現歷史場景、人物、細節等方面無與倫比的便捷優勢及其強大的畫面表現力,越來越受到創作者的青睞。不過同時也帶來了更大的爭議,因為動畫是一門帶有主觀性和虛構性特征的藝術,能夠“虛擬”再現構想中的任何場景,藝術語言和技術手段的虛構性與紀錄片“真實性”的基本原則形成一對矛盾,動畫藝術語言便是這樣帶著巨大的爭議在歷史題材紀錄片中得以廣泛運用。
動畫藝術語言在歷史題材紀錄片創作中的運用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電腦動畫的門檻不斷降低,各種制作軟件的普及和專業人才的增多使動畫藝術的應用范圍不斷擴展,成為電影、電視、廣告、欄目包裝等領域不可或缺的創作元素。近年來,動畫藝術語言在紀錄片創作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尤其在歷史題材紀錄片中,動畫成為再現歷史場景、彌補史料不足的有力武器。動畫在歷史題材紀錄片中的運用現狀及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藝術化再現歷史情景,增加生動性。比如紀錄片《我的抗戰》貫徹了創作者“口述歷史”的理念,通過對當事人的采訪記錄歷史,為了提高整部作品的生動性與藝術價值,創作者采用了木刻版畫風格的動畫形式作為輔助手段,通過動畫場景與當事人敘述的聲畫組合營造出強烈的感染力,同時由于木刻版畫是抗戰時期流行的一種美術形式,使用這種動畫風格更在藝術精神層面與抗戰的歷史內涵相融合,使得整部作品的藝術價值大為提高。
其次,大幅降低了創作成本。仍然以《我的抗戰》為例,片中涉及到大量的戰爭場景,按照傳統的創作思路可以使用影視資料,不過現有的影視劇和相關紀實資料存在重復使用的現象,并且不同的影視素材剪輯不能保證整部作品視覺風格的統一,所以這條思路沒有被創作者采納。如果使用真實再現,場景、道具、爆破以及影視設備的使用勢必造成成本大幅增加,還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動畫藝術語言的運用輕松地解決了以上問題,節省了大量成本,使創作者有更多精力放在歷史事實的挖掘采訪和提高作品的藝術水平上。
再次,提高了畫面表現力,更適合史詩場景的再現。在《圓明園》中,創作者面臨著空前的難題,因為圓明園已經毀于戰火,僅有遺跡存留。由于年代久遠,當事人都已經離世,只留下些許文字與圖片記錄,以如此匱乏的可視性材料去創作一部時長90分鐘紀錄片的難度可想而知。此時真實再現理應成為創作者的首選,但是如果要達到視覺“復原”圓明園的創作目標,場景的搭建將會是一項浩瀚的工程,絕不是一個紀錄片劇組所能完成的;若采用模型搭建的方式則難以展現園林恢弘的史詩場面和建筑精美的細節,畫面表現上會留有遺憾。最后創作者選擇了三維動畫,通過建模、材質技術可以完美地表現任何建筑細節,利用高性能計算機可以完成大規模建筑群和風景的渲染,再加上精心設置的漫游動畫,使觀眾隨著虛擬攝像機的運動在圓明園的數字化史詩幻境中移步換景。
又次,擴展了題材與表現范圍。動畫藝術語言使歷史題材紀錄片擺脫了長久以來可視性材料缺乏對創作的束縛,創作者可以放開手腳去選擇他們過去所無法駕馭的對象。近年來,一大批歷史題材紀錄片借助動畫藝術語言為觀眾呈現了過去未曾表現過的題材,如《大唐西游記》巧妙地用動畫形式呈現了調查玄奘師徒取經真實性的整個過程;表現中華五千年文明及“天人合一”理念的《故宮》通過動畫再現了紫禁城建造過程和浩大典禮儀式等歷史場景;獲得金球獎最佳影片獎的動畫紀錄片《和巴什爾跳華爾茲》甚至利用動畫藝術語言完成了對回憶、夢境和心理的紀錄。最后,使歷史紀錄片更富有時代氣息。影像技術的進步和創作手法的多元化使影視劇的創作極富時代氣息,如《阿凡達》、《盜夢空間》等影視作品都獲得了極高的社會關注和回報。“一直以來,中國紀錄片重視內在屬性,而對形式的審美性缺乏必要的關注”[2],我們應當在保證歷史真實的基礎上,不斷豐富紀錄片的視聽語言與創作手法,動畫藝術語言無疑給創作者提供了又一種可能。
總之,動畫藝術語言為歷史題材紀錄片帶來的改變是顯而易見的,成為歷史題材紀錄片創作者的一把利器,使他們的創作不再受到缺乏可視性材料這一問題的束縛,大大開拓了歷史題材紀錄片的表現范圍。
動畫藝術語言與真實再現手法之比較
動畫藝術語言的運用為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動畫藝術語言主觀、虛擬性的特征與紀錄片的真實性要求之間的矛盾是繞不過的問題,本文通過對動畫藝術語言與真實再現的比較,分析二者與紀錄片真實性原則的關系。當下也有人將紀錄片中的動畫場景歸為“真實再現”,這是一種廣義的劃分方法,認為二者都運用藝術化手段將過去式的歷史場景予以視聽重現,這種重現是真實歷史場景的“模仿”而非復原,從這個角度看二者是相同的。但這混淆了動畫與真實再現藝術創作的本質區別,真實再現以影視造型語言為基礎、以“搬演”為形式,經過每個場景逐個鏡頭的拍攝剪輯完成,對美工、服裝、道具、燈光的要求與影視劇基本相同;而動畫藝術語言以美術造型語言為基礎,由動態的線條與色彩構成,具有很強的主觀虛擬性、表意抽象性,不需要場景與演員,尤其是在數字動畫藝術語言的支撐下,僅需要幾臺電腦就可以進行創作。
真實再現彌補了歷史題材紀錄片表現手法不足的缺點,增強了可視性與生動性,“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紀錄片的一次自我救贖,把自己從解說詞加圖片的刻板中解放了出來,拓寬了紀錄片的表現領域和敘述空間”[3]。但是從接受角度講,真實再現常常引導觀眾進入“故事”情境,產生所見即真實歷史場景的錯覺,而且拍攝過程中的場景、道具、服裝、表演越真實,給觀眾造成的錯覺就越大,比完全采用虛擬風格的動畫藝術語言更容易將觀眾帶離對歷史真實的探求。比如《圓明園》中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相聚的一段真實再現,畫面唯美、鏡頭精到,使觀眾在“故事片”觀看與“紀錄片”欣賞之間產生了游離,雖然畫面中的演員、服裝、建筑等等都是處于“再現”情景中的歷史表義符號,但是由于與生活中的現實場景具有絕對的視覺關聯性,所以很容易讓觀眾得出片中的假定情景就是歷史場景的最終結論。
在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創作中,真實再現與動畫藝術語言都能夠做到“非虛構”,但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歷史紀錄片中“歷史真實”與“影視藝術化處理”的界限;而動畫藝術語言“得益于這樣一種獨特的辯證法: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關于真實人物,同時我們也知道自己正在看的是一種動畫方式的重構,它與現實并沒有那種我們所熟知的索引性關聯”[4],這樣就避免了由假定場景中的具象視覺符號造成的審美混亂。動畫語言明確地告訴觀眾,虛擬的動畫場景可以做到所表現的歷史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等各個要素都符合歷史真實的客觀要求,但并不要求畫面中建筑、街道、衣服的細節完全等同于所講述的歷史時間、地點中的真實情景。這樣,動畫藝術語言通過假定場景中的假定性視覺符號反而能夠讓觀眾跳出對假定場景的“執著”,將審美重心放在對歷史事件的把握上,去體驗和思索創作者所要表現與傳達的歷史真實。
動畫藝術語言與紀錄片“真實性”原則
通過以上比較我們看到,動畫藝術語言通過一種“陌生化”的方式將觀眾帶出了真實再現所造成的“真實還是故事”的困惑,但由于藝術形式的高度假定性,還是使其在有關“真實性”的問題上飽受爭議。其實在創作實際中,動畫藝術語言并不僅限于歷史題材,而是在各種題材紀錄片創作中都得到了廣泛運用,并且還發展出專門使用動畫藝術語言進行創作的“動畫紀錄片”:“在動畫紀錄片創作中,創作者可以將動畫所要表現的對象進行放大,甚至擴展到整部影片,通過對形式、風格的把控,動畫成為一種重要的修辭手段,賦予影片主題以非同尋常的意味”。[5]這類紀錄片使用動畫藝術語言表現真實事件,最早可追溯到1918年的《路西塔尼亞號的沉默》,華裔導演王水泊1998年創作的《天安門上太陽升》曾獲得1999年奧斯卡最佳短紀錄片提名,近幾年的代表就是反應黎巴嫩戰爭的《和巴什爾跳華爾茲》,在這些優秀的動畫紀錄片中,“一方面所描述的事實來源于現實世界,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另一方面影片又完全是風格化的、表現主義的,有著虛構的外觀。這里潛在著的是動畫紀錄片在認識論上較之與傳統的紀實風格紀錄片的某種偏移。”[6]
可見動畫技巧屬于紀錄片的風格層面,而真實性屬于紀錄片的本質范疇,二者并不在一個比較層面,“不管一部影片是攝像機實拍的還是動畫制作的,不管它是紀實主義的還是表現主義的,與它是否可以成為紀錄片沒有關系。這里惟一的標準是觀眾是否在觀影的過程中,循著影片的線索,將自己的思維、情感指向我們生存其中的現實世界”[7],所以不能片面地因為風格層面的藝術語言帶有一定的虛構性而否定歷史題材紀錄片的本質真實。猶如美術創作中的新技法只是給畫家提供了一種新的造型可能性,動畫藝術語言之于紀錄片也只是一種材料與手段的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講,動畫藝術語言和紀實手法一樣本身都不帶有主觀虛構性,也不帶有客觀紀實性,關鍵在于創作者以什么樣的方式使用它,以紀實手法拍攝的不一定是真實的,比如《一個都不能少》;而全篇采用動畫藝術語言也可以是歷史題材紀錄片,比如《和巴什爾跳華爾茲》。可見創作者對技術手段的運用態度和把握尺度才是紀錄片真實性的保障,所以在使用動畫藝術語言輔助創作時必須以嚴格把握歷史事件的真實性為前提,不能主觀地通過動畫去實現歷史臆想。動畫藝術語言的使用要有一定的限度,如果經過努力能夠做到實拍,那還是要讓觀眾看到最真實的歷史場景,即便是只剩下遺址、遺跡、文物、文獻,這也是觀眾有權利看到的最貼近歷史真實的圖像,在此之外可以使用動畫藝術語言作為輔助,補充動態的歷史圖景,使創作更為豐滿,如果沒有原則地濫用動畫藝術語言,那就將歷史題材紀錄片帶進了創作的誤區。
綜上,動畫藝術語言為歷史題材紀錄片提供了有力的創作工具,使其能夠以更小的成本解決可視性材料缺乏的問題,為拓展題材、提高表現力提供了可能。雖然藝術語言帶有主觀虛擬性和假定性,但不能簡單地認定運用動畫再現歷史場景就是違背“真實性”原則,因為語言層面的虛擬性不能否定藝術作品的本質真實,相反只要有嚴肅的創作態度,在把握歷史真實的前提下合理運用動畫藝術語言能夠實現歷史題材紀錄片真實性追求和詩意性審美的雙重目標。
本文html鏈接: http://m.cssfps.cn/qkh/283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