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司法人工智能的不斷完善和深度應(yīng)用,人類法官正在或者已經(jīng)讓渡部分決策權(quán)成為不爭的事實。相較于人類法官,司法人工智能的經(jīng)驗更加豐富、立場更加客觀、運轉(zhuǎn)更加高效。因而有觀點認(rèn)為,司法人工智能將全面取代人類法官展開審判工作。但經(jīng)驗不止于數(shù)據(jù),中立不同于孤立,高效不等于質(zhì)優(yōu)。受制于司法人工智能在知識結(jié)構(gòu)、應(yīng)用場景以及潛在能力上與人類法官的差異,司法人工智能只能成為法官的“助手”而不是“替身”。尤其是當(dāng)面對一些疑難、復(fù)雜、新型案件時,司法人工智能是無能為力的,這些案件只能交由人類法官作出裁判。面對著人工智能時代的挑戰(zhàn),法官群體也需要積極轉(zhuǎn)變角色和職能:其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輔助裁判功能,努力成為更理性化的法官;其二,充分發(fā)揮人類的良知、正義感和同情心展開境遇想象和情感互融,努力成為更溫情化的法官;其三,在提升自身專業(yè)素養(yǎng)、審判經(jīng)驗的同時,積極學(xué)習(xí)人工智能相關(guān)知識和技能,努力成為更精英化的法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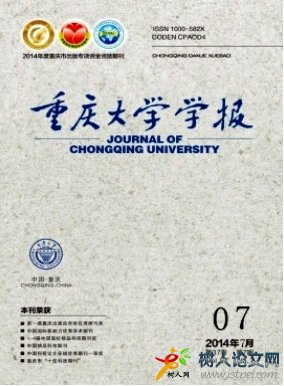
本文源自陳銳; 王文玉, 重慶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 發(fā)表時間:2021-07-27
關(guān)鍵詞:司法人工智能;人類法官;角色定位;司法經(jīng)驗;價值判斷
隨著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神經(jīng)科學(xué)、區(qū)塊鏈、語音文字識別等領(lǐng)域技術(shù)的突破,人工智能迎來了新一輪的發(fā)展高潮,一系列工作崗位已經(jīng)或正在被更安全、高效、經(jīng)濟(jì)的機(jī)器所取代。甚至是人類法官,這一曾被認(rèn)為最不可能被機(jī)器取代的崗位之一,也開始面臨著人工智能的挑戰(zhàn)。隨著司法人工智能的不斷完善和深度應(yīng)用,人類法官正在或者已經(jīng)讓渡部分決策權(quán)成為不爭的事實。有學(xué)者指出,若人工智能不但可以提出有說服力的論點,還能在判決書的寫作方面超越人類法官,那么,可靠性并不遜色于人類且成本效益更優(yōu)的人工智能就應(yīng)當(dāng)被視為法官[1]。當(dāng)前,已經(jīng)有人工智能在司法實踐中表現(xiàn)出了優(yōu)于人類法官、專家的裁判預(yù)測準(zhǔn)確率。如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大學(xué)與南德克薩斯法學(xué)院以美國最高法院 1791 至 2015 年的數(shù)據(jù)信息為基礎(chǔ),開發(fā)了一種算法,在對 1815 至 2015 年間最高法院法官的決定和投票展開預(yù)測時,其準(zhǔn)確率高達(dá) 70.2% 和 71.9% ,已經(jīng)超越了法學(xué)家 66%的預(yù)測準(zhǔn)確率[2]。縱使如此,本文仍認(rèn)為,一方面,我們應(yīng)當(dāng)理性地看待司法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挑戰(zhàn),即使是仍然處于猜想階段的強(qiáng)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也并不意味著人類法官的工作會被完全替代;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接受人工智能時代到來的事實,積極推動法官①角色和功能的轉(zhuǎn)型升級,以回應(yīng)人工智能時代對法官角色定位的新需求。
一、司法人工智能相較于人類法官的優(yōu)勢
在新一輪人工智能浪潮中,人們不再熱衷于通過某一人形機(jī)器人的發(fā)明以全面替代人類在所有領(lǐng)域的思考或勞動,而是希望機(jī)器人能夠在某一領(lǐng)域替代人類的體力或腦力勞動。即依照控制論的觀點,只要機(jī)器能夠在某一領(lǐng)域內(nèi)做和人一樣的事情,就可以被稱之為人工智能。本文所指的人工智能自然是能夠模擬法官展開司法裁判的機(jī)器或者系統(tǒng)。若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領(lǐng)域能夠模擬法官所做的活動,達(dá)到以假亂真甚至是超越法官的效果,那么人工智能成為法官的“替身”,替代法官展開司法裁判將是可能的和值得被期待的。從當(dāng)前人工智能在司法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實踐和發(fā)展前景來看,人工智能在以下幾個方面有著人類法官所不具備的優(yōu)勢。
(一)經(jīng)驗更豐富的司法人工智能
面對詹姆士一世“國王為何不能當(dāng)法官”的質(zhì)疑,柯克大法官指出,“法律乃是一門藝術(shù),一個人要想獲得對它的認(rèn)識,需要事先經(jīng)歷長期的學(xué)習(xí)和實踐”[3]。究其原因,司法是一項理性化的事業(yè),需要法官豐富的審判經(jīng)驗才能夠處理好法律的適用、糾紛的解決、正義的弘揚、社會有序化的引導(dǎo)等一系列事關(guān)重大但又難以拿捏分寸的事項。由于經(jīng)驗不同于全稱命題或判斷,其是對事物之間常態(tài)聯(lián)系的一種不完全歸納,因而經(jīng)驗的蓋然性程度和歸納樣本數(shù)量的大小息息相關(guān)。與人類通過長期訓(xùn)練以及審判實踐獲得經(jīng)驗的方式不同的是,擁有數(shù)據(jù)存儲、閱讀以及算法、算力優(yōu)勢的司法人工智能可以對海量數(shù)據(jù)的全部樣本展開分析和學(xué)習(xí),掌握法官群體所積累的共性經(jīng)驗,獲得更為開闊的法律視野和更為豐富的司法實踐知識,從而輕易超越人類法官智慧的“臨界點”。
如在事實認(rèn)定中,當(dāng)證據(jù)和待證事實之間的關(guān)系不確定時,司法人工智能可以根據(jù)對大量先例經(jīng)驗的學(xué)習(xí),量化證據(jù)要素和事實結(jié)論之間的蓋然性,從而避免在不確定條件下,法官囿于個人知識和經(jīng)驗的不足而忽略一些重要的案件信息,作出不合理甚至錯誤決斷的風(fēng)險。在實踐探索中,貝葉斯公式能很好地描述在新證據(jù)被引入之后,如何調(diào)整依照初始證據(jù)所認(rèn)定事實的蓋然性程度[4]。又如在對事實展開評價時,司法人工智能基于對法官整體經(jīng)驗的學(xué)習(xí),不但能夠嚴(yán)格依照先例對簡單案件作出具有可預(yù)測性的裁判,且對于疑難、復(fù)雜、新型等法官個體經(jīng)驗不足以有效應(yīng)對的案件,司法人工智能也可以通過對法官集體生活經(jīng)驗和整體理性的發(fā)掘而作出更加可靠、穩(wěn)定的判決,避免法官個人通過臆想展開裁判的不確定性風(fēng)險。因而有學(xué)者指出,“相較于那些沒有宣布法律原理發(fā)生廣泛變化的案件,在依賴司法裁量權(quán)的普通案件中,機(jī)器能夠更加有效地預(yù)測案件的裁判結(jié)果”[5]。
司法人工智能相較于人類法官經(jīng)驗更加豐富的優(yōu)勢還體現(xiàn)在對同案同判目標(biāo)的實現(xiàn)上。同案同判是保障司法裁判平等性和安定性的基本要求,也是通過司法裁判向社會輸出穩(wěn)定的行為規(guī)則信號,從而實現(xiàn)社會行為有序化的重要方式。德沃金認(rèn)為,“同案同判所要求的不外乎是法院對所有的人都以一個相同且具有融貫性的方式行動,把自己對某些人適用的公平或正義的實質(zhì)性標(biāo)準(zhǔn),擴(kuò)張至每個人”[6]。但在實踐中,同案不同判現(xiàn)象的存在已經(jīng)成為困擾我國司法公正性的頑疾,其會引發(fā)民眾對法官裁量正當(dāng)性和合法性的質(zhì)疑,最終將有損于司法公信力的建構(gòu)[7]。隨著司法改革的深入,司法公開的進(jìn)一步完善,同案不同判現(xiàn)象對司法的權(quán)威性、社會認(rèn)同性所造成的損害將進(jìn)一步加大[8]。
豐富的經(jīng)驗對于應(yīng)對同案不同判難題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這種經(jīng)驗的掌握不在于審判實踐的歷練,僅僅在于掌握的先例數(shù)量以及對先例中各要素與裁判結(jié)果相關(guān)性的總結(jié)程度。顯然,與人類法官相比,司法人工智能在對先例這一審判實踐經(jīng)驗的掌握上有著明顯優(yōu)勢。大數(shù)據(jù)把司法歷史編纂成書,算法為這本書籍繪制出清晰的知識圖譜和簡潔的索引目錄。司法人工智能在司法信息的存儲、查詢和分析能力上相較于法官個體有著巨大的優(yōu)勢。如我國建立的裁判文書網(wǎng)已經(jīng)有突破 1 億份的裁判文書,面對浩如煙海的先例,法官個體想要瀏覽一遍這些文書是不可能的任務(wù),更不用說對這些文書的要素予以全面掌握。而司法人工智能則能夠憑借算法和算力的優(yōu)勢,對這些文書展開深度學(xué)習(xí)、知識計量和圖譜繪制,并挖掘其中隱含的動態(tài)相關(guān)性規(guī)律。當(dāng)有類似的裁判要素被輸入之后,司法人工智能可以根據(jù)要素的相關(guān)度關(guān)聯(lián)先例中所隱含的裁判知識鏈,并給出與之相匹配的案件裁判結(jié)論或量刑幅度等。隨著司法自動化程度的提升,司法人工智能有希望習(xí)得從立案到執(zhí)行的全程數(shù)據(jù),這意味著通過對海量全樣本數(shù)據(jù)的學(xué)習(xí),司法人工智能將在可量化維度上,擁有遠(yuǎn)遠(yuǎn)超出法官個體能力的知識和經(jīng)驗。
(二)立場更客觀的司法人工智能
達(dá)瑪什卡在描述理想的糾紛決策者時,指出在實際的糾紛之中,由于“民眾清醒地認(rèn)識到訴訟結(jié)果是不確定的,且正確的結(jié)果是一種難以獲得的奢侈品,因而他們期待的無非是從決策者那里能夠得到平等的對待——也即希望決策者能夠保持一種中立的、客觀的或公允的姿態(tài)。”其提出,理想的決策者一方面應(yīng)當(dāng)是依靠當(dāng)事人所提供的、經(jīng)過當(dāng)事人辯論過濾后的信息,而不是法官主動開辟信息渠道所獲得的信息;另一方面,理想的決策者應(yīng)當(dāng)處于一種白板狀態(tài),“如果決策者是對當(dāng)事人之間的法律論辯保持開放狀態(tài)的空白接收器,那么糾紛解決程序就會顯得更加純粹,也能保持一種高水平的運轉(zhuǎn)狀態(tài)”[9]。客觀、中立的立場既是保障司法過程公正性的重要因素,也是司法裁判獲得民眾認(rèn)同的前提。然而,實踐表明,由于法官個體的喜好、偏見、倦怠、腐敗等問題,希冀人類法官保持中立、客觀或公允的姿態(tài)是一種難以獲得的奢侈品。“無論是作為一個群體還是個人,人類法官都是出了名的不一致。任何一個法官對環(huán)境的敏感性和對寬大處理的偏好也會隨著他們是餓了、累了、無聊了、工作過度了、不知所措了還是分心了而發(fā)生巨大的變化”[10]。
與人類法官相比,司法人工智能的立場顯然更加中立和客觀。理查德和艾麗西婭指出,使用人工智能裁決潛在的好處是雙重的,“首先,因為一個相同的算法可以解決每一個相關(guān)的爭議,人工智能裁決可以減輕,甚至消除由于在意‘好法官或富有同情心的法官’的名聲而導(dǎo)致的任意性裁決。其次,裁決過程本身的標(biāo)準(zhǔn)化可以兌現(xiàn)成文法中關(guān)于正義的司法承諾,消除司法決策中的人為偏見”[11]。司法人工智能的基本運作機(jī)理是以司法大數(shù)據(jù)為樣本,通過語義分析和數(shù)據(jù)分析建模,從而逐一甄別數(shù)據(jù)樣本中可能影響裁判結(jié)論的相關(guān)因素,然后將這些數(shù)據(jù)打上相應(yīng)標(biāo)簽并整合成結(jié)構(gòu)化的知識鏈條,最終實現(xiàn)精準(zhǔn)的自動化裁判。這一注重司法各要素的可測量性、依靠獨立自主的算法、能夠重復(fù)應(yīng)用的法律系統(tǒng)可以有效擺脫人類法官自由裁量的任意性,推動法律的統(tǒng)一適用,消除法官主觀價值偏見以及案外因素對裁判可預(yù)測性的影響,最終保障司法裁判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雖然當(dāng)前司法人工智能還無法完全替代法官展開裁判,但其已經(jīng)被廣泛用于諸如量刑、賠償金額的計算、證據(jù)的審查等法官自由裁量領(lǐng)域,實踐表明其在避免法官裁量的肆意性方面效果顯著。如美國的一些州已經(jīng)使用 COMPAS 對被告展開再犯風(fēng)險評估,并由此確定刑期的長短[12]。當(dāng)被告盧米斯認(rèn)為 COMPAS 對其量刑過重,違背程序正當(dāng)性而上訴時,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對其訴訟請求予以駁回,并指出:“COMPAS 系統(tǒng)對風(fēng)險展開評估并決定量刑的功能,是通過具有獨立性的子項以及復(fù)雜的算法來實現(xiàn)的,其最終得出 1-10 的評定級別,這一算法系統(tǒng)具有中立性和客觀性,因而是符合程序正義的。”[13]隨著技術(shù)的發(fā)展成熟,司法人工智能會被更加廣泛用于司法決斷的諸多領(lǐng)域,其客觀、中立的立場將會顯著提升司法裁判的可預(yù)測性和可接受性。
(三)運轉(zhuǎn)更高效的司法人工智能
貝卡利亞曾用“法官懶懶散散,而犯人卻凄苦不堪”[14]來表明司法效率的重要性。但當(dāng)前,情況又有所不同。隨著法治理念在全球的確立,訴訟爆炸引發(fā)的司法案多人少的困境不但使當(dāng)事人遭受司法的負(fù)累,甚至法官也不堪其苦:過多案件的壓力不但使辦案質(zhì)量遭受考驗,還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法官的流失。雖然我國采取了諸如打造多元化糾紛解決機(jī)制、推動案件繁簡分流改革、優(yōu)化審判管理制度等措施,希望能夠緩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但在不改變原有裁判產(chǎn)出方式的背景下,通過深挖現(xiàn)有制度潛力的探索并沒有給司法效率帶來實質(zhì)性變革。而借助強(qiáng)大的算法、算力以及憑借標(biāo)準(zhǔn)化、流程化、重復(fù)性的特點,司法人工智能可以在短時間內(nèi)完成需要大量人工和時間才能完成的諸如證據(jù)審查、案卷制作、要素式裁判文書的生成等工作,從而以變革生產(chǎn)工具的方式推動司法效率的提升,有效緩解案多人少的司法困境。
當(dāng)前司法人工智能主要從以下方面提升司法效率。在司法信息處理智能化方面,人工智能法律系統(tǒng)在在線立案、在線開庭、證據(jù)審查、審判信息自動生成等方面可以有效節(jié)省人工和耗時成本。如蘇州中院開發(fā)的庭審語音識別系統(tǒng),能夠自動區(qū)分不同庭審發(fā)言對象,且語音識別準(zhǔn)確率達(dá)到 90%以上。實踐統(tǒng)計表明,其可以將庭審時間縮短 20%-30%,對于一些復(fù)雜案件,庭審時間能減少 50%以上,且庭審記錄的完整度也達(dá)到 100%[15]。又如在達(dá)席爾瓦·摩爾訴陽獅集團(tuán)一案中,法官充分運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上的優(yōu)勢,對多達(dá) 300 萬份的數(shù)據(jù)展開清理工作,將其中大量與案件無關(guān)的數(shù)據(jù)剔除出去②。在文書制作自動化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文字識別、圖像識別、語義分析、要素關(guān)聯(lián)等技術(shù)將案件的相關(guān)材料予以解構(gòu),并依照給定的知識圖譜重新組合,從而自動生成簡明扼要的令狀式、要素式、表格式等的裁判文書。當(dāng)前,對于一些交通損害賠償、銀行合同借貸以及政府信息公開等事實清楚、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明確、雙方爭議不大的類型化案件,通過裁判文書自動生成的方式可以大幅縮減法官的工作量 [16]。如重慶市以信用卡、金融借款類案件為突破口,通過將案件審理規(guī)則要素化并嵌入案件審理全過程的方式開發(fā)了供法官使用的“智能專審”系統(tǒng),這一系統(tǒng)可以智能收集、整理庭審階段所確認(rèn)的信息并自動生成令狀式的裁判文書[17]。又如海南法院運行的量刑規(guī)范化智能輔助系統(tǒng),在量刑規(guī)范化的案件中,將裁判文書制作時間縮短近 70%,程序性法律文書的制作時間更是減少近 90%[18]。
雖然司法人工智能在這些方面的應(yīng)用還沒有達(dá)到完全自動化的程度,但當(dāng)前的探索實踐已經(jīng)表明人工智能在提升司法效率方面擁有顯著的優(yōu)勢。如“河北在全省 178 個基層法院上線的‘智審 1.0’審判輔助系統(tǒng),幫助法官減少了近 30%的工作量,大幅提升了審判質(zhì)效” [19]。“貴陽政法大數(shù)據(jù)辦案系統(tǒng)在花溪區(qū)和經(jīng)開區(qū)試運行期間,將辦理同類案件的時間同比縮短了 30%,同時案件辦理質(zhì)量也得到了顯著提升”[20]。隨著技術(shù)的進(jìn)步和完善,人工智能一旦應(yīng)用于從立案到執(zhí)行的司法全過程之中,那么司法裁判的效率將會得到質(zhì)的飛躍,阻礙司法正義的案多人少難題也將得到徹底解決。
二、只能作為法官“助手”而不是“替身”的司法人工智能
雖然從當(dāng)前的司法應(yīng)用實踐來看,司法人工智能尚處于開發(fā)和探索階段,許多工作還需要在法官的輔助下完成。但延續(xù)上文司法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趨勢,隨著技術(shù)的成熟和實踐應(yīng)用的深化,司法人工智能的這些優(yōu)勢會進(jìn)一步被放大,法官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似乎已經(jīng)在所難免。但在對司法人工智能的可能空間與內(nèi)在限度展開更加深入的探究之后,不難發(fā)現(xiàn),司法人工智能存在著知識結(jié)構(gòu)、應(yīng)用場景以及潛在能力上的缺陷,這些缺陷決定了其只能成為法官的“助手”,而不是“替身”。
(一)經(jīng)驗不止于數(shù)據(jù)
司法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夠復(fù)制人類法官的裁判經(jīng)驗,在于其可以通過對被數(shù)據(jù)化的司法信息的學(xué)習(xí),掌握要素之間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并將這些數(shù)據(jù)經(jīng)驗運用于決策之中。但顯然,數(shù)據(jù)化的經(jīng)驗和司法裁判中實際需要的經(jīng)驗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經(jīng)驗知識都能夠以數(shù)據(jù)化的方式表達(dá),許多知識需要決策者的參與、經(jīng)歷和感悟才能夠獲得,而這些知識的獲得是無身性的人工智能所力不能及的。要想作出適當(dāng)?shù)牟脹Q,決策者不但需要掌握法律知識,還需要掌握“庭審說話的藝術(shù)”“化解糾紛的技巧”“發(fā)掘隱含爭議的能力”“傾聽當(dāng)事人情感和心理需求的耐心”等等,才能合理地處理鑲嵌于社會生活之中的法律糾紛。顯然,這些知識都來自于法官長期的社會生活以及司法裁判經(jīng)驗,而以單一的案例或法規(guī)數(shù)據(jù)庫為經(jīng)驗來源的司法人工智能往往難以掌握這些綜合性的、親身體驗性的、需要要素遷移和聯(lián)想的知識。這些需要通過對真實物理世界的長期參與和主動感知才能習(xí)得的知識也很難通過數(shù)據(jù)化的方式簡化為“一種無須滿足任何更多的條件即可生成‘是’與‘否’的二元選項的代碼”[21],這決定了司法人工智能的應(yīng)用只能夠被限縮在一些只需要單一的知識結(jié)構(gòu)、有明確對錯答案以及存在可辨別的潛在模式和結(jié)構(gòu)的場景之中[22]。
其次,數(shù)據(jù)化的經(jīng)驗往往只是明示的經(jīng)驗,而明示信息背后許多默會的、隱性的因素?zé)o法通過數(shù)據(jù)化的方式被人工智能習(xí)得,這造成司法人工智能所依賴的數(shù)據(jù)經(jīng)驗是一種片面的經(jīng)驗。裁判文書是當(dāng)前司法人工智能系統(tǒng)建構(gòu)的基礎(chǔ)性資產(chǎn),然而實踐中許多影響決策結(jié)果的關(guān)鍵行為信息卻是高度非文字化和非數(shù)據(jù)化的,其并不會反映到裁判文書之中。如法官的學(xué)歷、性格、生活經(jīng)歷、個人偏好,法官心證的過程,合議庭、審委會的討論情況,當(dāng)事雙方訴訟文書的質(zhì)量,社會輿論的波動,人情、行政的介入等等,這些重要但被掩蓋的隱性因素是人工智能無法習(xí)得的。因而有學(xué)者指出,“人工智能對審判經(jīng)驗的吸收和設(shè)計者對經(jīng)驗的標(biāo)準(zhǔn)化和規(guī)范化總結(jié)僅是審判所需經(jīng)驗的很小一部分,人工智能僅是對智性部分模仿的初級階段”[23]。片面的經(jīng)驗無形中會放大和固化司法人工智能決策的偏差性,進(jìn)而影響其決策的穩(wěn)定性和可接受性。
最后,司法人工智能只能延續(xù)過去的經(jīng)驗,無法創(chuàng)造未來。經(jīng)驗的適用是司法裁判的形,而經(jīng)驗的創(chuàng)制才是司法裁判的魂。法律不可朝令夕改,但也不可一成不變,其需要根據(jù)社會發(fā)展需求而適時發(fā)生變動。“穩(wěn)定性和確定性本身并不足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還必須服從進(jìn)步所提出的正當(dāng)要求”[24]。運動與靜止、保守與創(chuàng)新、守成與變遷之間的辯證平衡,正是法律生命力的來源。由于立法的滯后性,司法往往是社會需求的前沿崗哨,當(dāng)社會價值變遷以致獲得民眾廣泛認(rèn)同時,就需要法官通過法律解釋、法律創(chuàng)制等方式適時地推動法律發(fā)展,從而實現(xiàn)法律的穩(wěn)定性與適應(yīng)性在社會需求變革以及技術(shù)創(chuàng)新發(fā)展背景下的平衡。只能學(xué)習(xí)以數(shù)據(jù)化方式呈現(xiàn)的過去經(jīng)驗而無法創(chuàng)制新經(jīng)驗的司法人工智能,反而會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技術(shù)—法律鎖定效應(yīng)”,造成法律的停滯和僵化③。經(jīng)驗的應(yīng)用和經(jīng)驗的創(chuàng)制之間是一種重復(fù)與創(chuàng)造的關(guān)系,只要作為司法裁判靈魂的經(jīng)驗創(chuàng)制把握在法官手中,法官被司法人工智能所替代的論斷就無法成立。
(二)中立不同于孤立
雖然司法人工智能本身是客觀、中立的,但由于“喂養(yǎng)”人工智能的裁判文書并沒有排除價值判斷,因而司法人工智能是否真的如其所宣稱的那樣客觀、中立是存疑的。此外,司法正義的特性也決定了司法裁判并不能完全脫離價值判斷和生活情境而孤立展開。
首先,司法人工智能不可避免會學(xué)習(xí)到內(nèi)含于裁判文書中的人類法官原有的價值傾向,從而影響其決策的客觀、中立性。雖然司法人工智能本身能夠中立、客觀地展開裁判,但通過裁判文書“喂養(yǎng)”的方式,法官的價值傾向早已融入司法人工智能的基因之中。人工智能通過對已有裁判文書的分析、挖掘、歸納、提煉,從而對法官過往的裁判展開精準(zhǔn)畫像和深度學(xué)習(xí),最終依照法官決策要素之間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對裁判結(jié)果作出預(yù)測。雖然司法人工智能算法預(yù)設(shè)了其不受主觀價值判斷干涉的中立地位,但“喂養(yǎng)”人工智能的裁判文書卻可能早已暗含法官的個性甚至偏見。在“偏見進(jìn),則偏見出(Bias In,Bias Out)”定律[25]的影響下,司法人工智能算法會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價值偏差,從而偏離客觀公正的軌道。
如有學(xué)者在對美國司法系統(tǒng)所使用的預(yù)測被告人再次犯罪及其危險程度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 COMPAS 的裁判傾向展開了統(tǒng)計分析后,發(fā)現(xiàn)黑人所得分?jǐn)?shù)和白人所得分?jǐn)?shù)相比要高出 45% 左右[26]。又如,在一些樣本案例數(shù)量偏少的新型案件中,少數(shù)法官的價值偏見可能對司法人工智能裁判結(jié)論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基于大數(shù)據(jù)、互聯(lián)網(wǎng)、自主迭代算法的司法人工智能的價值偏見往往是隱含的,難以被輕易感知和發(fā)現(xiàn),而人工智能又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能力,故司法人工智能所習(xí)得的價值偏見等會隨著機(jī)器的反復(fù)、大量實踐而被進(jìn)一步固化,這些因素決定了司法人工智能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客觀和中立。
其次,司法實踐中的價值判斷是不可避免的,而這正是脫離了社會情境、保持“中立” “客觀”的司法人工智能無法自主決策的。認(rèn)為司法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法官的觀點基于以下論斷:擁有穩(wěn)定的適用對象(案件),明確的適用前提(法律文本和案件事實),遵守嚴(yán)格的程序,并且需要得出唯一確定性的裁決結(jié)論,因而司法裁判是一項客觀的、可以排除主觀價值判斷的事業(yè)。司法的這些特性似乎完美契合了人工智能的形式邏輯內(nèi)核,自然成為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典型樣本和最佳對象[27]。但在具體實踐中,無論是事實的認(rèn)定還是對法律規(guī)定的理解和適用往往都不會以理想中明確的方式呈現(xiàn),其時常需要法官發(fā)揮主觀能動性,運用自由裁量展開一定的價值判斷,從而通過裁剪事實和解釋法律的方式,實現(xiàn)二者之間的貼合。如在“帕爾默殺害祖父案”“陜西開發(fā)商狀告自己違法案”中,排除價值判斷而簡單地將法律和事實予以拼接的裁判顯然違背了“任何人不得從自己的違法行為中獲利”這一一般性社會正義理念。在司法裁判中,價值選擇問題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德沃金指出,法律推理,便意味著需要將待決的、具體的法律問題,放置于涉及法律推演的諸多原則或政治之道德性的龐大系統(tǒng)之中展開考量。實際上,若你沒有將裁決經(jīng)過一個巨大的、由諸多復(fù)雜原則所組成的、能夠統(tǒng)攬全局的系統(tǒng)的過濾,那么這意味著你沒有對這一法律問題進(jìn)行過正確的思考[28]。在出現(xiàn)價值沖突或價值選擇難題時,唯有人類法官根據(jù)具體個案的實情,參照社會一般正義理念、時代發(fā)展需求、政策考量等因素展開道德衡量才能實現(xiàn)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
當(dāng)前實踐表明,無論是出于對人類尊嚴(yán)的考慮,還是價值的無法量化性,希冀司法人工智能展開價值判斷都是一種不可行的進(jìn)路[29]。有學(xué)者指出,人們可能會就案件的裁決為何是以此種方式而不是彼種方式展開爭論,這些爭論中往往都會涉及到一般常識和經(jīng)驗、先前的判例以及與公平正義相關(guān)的理念等,而這其中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早已超越了人工智能的能力限度 [30]。除了價值判斷之外,內(nèi)嵌于社會治理之中的司法,還需要承擔(dān)引領(lǐng)社會正義理念、化解潛在社會矛盾風(fēng)險、貫徹政策方針等職能,而這些是脫離社會情境的司法人工智能所無法理解和參與的。
最后,司法人工智能自動化決策的特性將當(dāng)事人排除于決策過程之外,其既無法深入?yún)⑴c訴訟過程,表達(dá)自己的訴求,也無法感知決策過程,獲得明確的決策理由,這將有違當(dāng)事人對程序正義的認(rèn)知,降低司法決策的可接受性。可信賴司法需要的是遵循程序正義的司法,程序正義雖然要求法官處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地對案件展開裁判。但研究表明,在對程序正義的感知中,中立性排在過程控制和可信度之后[31]。個人對程序正義的感知和信賴往往來源于司法程序?qū)Ξ?dāng)事人的開放程度:當(dāng)事人參與度越高,司法就越值得信賴。如卡斯珀等人在研究因重罪在監(jiān)獄服刑的 400 多名囚犯后得出結(jié)論:律師與他們在一起的時間,警察是否有尊嚴(yán)地對待他們以及他們在審前拘留中等待了多長時間等程序正義問題才是當(dāng)事人感知公平正義的決定因素[32]。顯然,只有在法官主導(dǎo)的司法程序中,當(dāng)事人才能真實感受到其和決策者之間緊密的個人聯(lián)系。這種當(dāng)事人能感知的過程控制是個人相信程序合法性的基礎(chǔ)。
但自動化的司法人工智能決策方式使當(dāng)事人參與法庭辯論并通過觀點交鋒更正或深入表達(dá)觀點的權(quán)利被隱沒,遞進(jìn)式的訴訟程序被階段化的論斷所替代,這將違反程序正義所希望達(dá)到的過程控制狀態(tài):當(dāng)事人既無法實質(zhì)性參與訴訟過程,也無法在訴訟進(jìn)程中向決策者完善或深化對案情的陳述。此外,法治是理由之治,可信賴的程序正義還需要法官向當(dāng)事人解釋其決策的理由或過程。而司法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困境使決策的透明度和可解釋性成為難題。人們只能得到“裁判自動售貨機(jī)”所吐出的最終判決,卻對“貨物”生產(chǎn)的過程一無所知。“不幸的是,實現(xiàn)高水平程序正義的一些因素與大數(shù)據(jù)算法本質(zhì)上是不兼容的:被告永遠(yuǎn)不會感覺到與決策者的個人聯(lián)系,這將降低他們的可信度,而且隨著計算機(jī)對所做決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們會感覺到更少的過程控制。„„只有當(dāng)算法的計算對受影響的人來說是透明和可理解的,算法才會顯得可信。不幸的是,眾所周知,大數(shù)據(jù)算法是不透明和不可理解的,有時甚至對那些應(yīng)用它們的人來說也是如此”[33]。
(三)高效不等于質(zhì)優(yōu)
對于司法裁判而言,正義的裁判意味著決策者能夠在最短時間內(nèi)作出最優(yōu)決斷。雖然司法人工智能在提升裁判的效率方面有著優(yōu)異的表現(xiàn),但限于其所學(xué)習(xí)的裁判文書的質(zhì)量以及數(shù)據(jù)和算法模型的顆粒化程度,司法人工智能產(chǎn)出的判決質(zhì)量往往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加之社會民眾對機(jī)器裁判苛刻的錯誤率容忍度,進(jìn)一步提升了機(jī)器替代法官的難度。
首先,裁判文書公開不全面以及裁判文書質(zhì)量良莠不齊等因素決定了司法人工智能的決策并不能達(dá)到預(yù)期的全面、準(zhǔn)確狀態(tài)。司法人工智能決策系統(tǒng)是通過學(xué)習(xí)以往法官裁判經(jīng)驗并作出分析和預(yù)測的系統(tǒng)。因而,司法數(shù)據(jù)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直接關(guān)系人工智能法律系統(tǒng)決策結(jié)果的合理性。但從具體的實踐經(jīng)驗來看,無論是司法數(shù)據(jù)的全面性還是優(yōu)質(zhì)性都面臨著一系列問題。以裁判文書為例,雖然我國已建立全世界規(guī)模最大的裁判文書數(shù)據(jù)庫,為人工智能法律系統(tǒng)提供了體量巨大的數(shù)據(jù)基礎(chǔ)。但事實上,我國裁判文書公開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全面。據(jù)學(xué)者統(tǒng)計,已公開的裁判文書的數(shù)量可能僅占審結(jié)案件的 50%左右[34]。并且由于裁判文書公開規(guī)范不足、監(jiān)管不力、人力資源緊缺以及公開裁量濫用等因素,這些公開的裁判文書還存在一句話文書、空白文書以及重復(fù)文書等情形,使裁判文書的質(zhì)量難以得到保障[35]。由于公開裁量的濫用,被隨意刪改、刪選后的上網(wǎng)文書會誤導(dǎo)機(jī)器的學(xué)習(xí),使人工智能在作出預(yù)測時面臨選擇性偏誤的風(fēng)險[36]。如果想要改善當(dāng)前情況,則需要對裁判文書數(shù)據(jù)庫展開清洗,而要對如此體量巨大的數(shù)據(jù)庫展開清洗顯然是一項費時費力的浩大工程。通過以上分析,可以解釋為何當(dāng)前許多司法人工智能審判模型的建構(gòu)往往是以某一地區(qū)、某一類案件中抽取的少數(shù)樣本案件為基礎(chǔ)展開的。這種建構(gòu)方式雖然保障了數(shù)據(jù)來源的優(yōu)質(zhì)性,但脫離了全樣本數(shù)據(jù)學(xué)習(xí)的司法人工智能,其客觀性和準(zhǔn)確性優(yōu)勢將會遭到削弱。
其次,司法人工智能決策的科學(xué)性有賴于精細(xì)化的數(shù)據(jù)和模型,但要實現(xiàn)二者顆粒化程度的提升還面臨著諸多技術(shù)上的難題,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工成本。當(dāng)前司法人工智能的主體算法往往是通過知識圖譜加深度學(xué)習(xí)的方式建構(gòu)的。“通過可視化的方式對案件展開精準(zhǔn)畫像的知識圖譜的可靠性依賴于數(shù)據(jù)和模型的顆粒化程度,模型和數(shù)據(jù)越精細(xì),知識圖譜的效果才越好”[37]。但要提升數(shù)據(jù)和模型的顆粒化程度并非易事:其一,需要面對機(jī)器語言和自然語言之間的轉(zhuǎn)化難題。機(jī)器語言和自然語言之間存在天然的差異,自然語言的多義性、語境化、模糊化等特征使通過詞向量轉(zhuǎn)化和分詞技術(shù)等抓取核心語素和語義為基礎(chǔ)的機(jī)器語言很難全面、準(zhǔn)確地識別和理解案件中的復(fù)雜語義。其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由于無法習(xí)得數(shù)據(jù)背后所隱含的影響法官決策的因素,司法人工智能所學(xué)習(xí)的數(shù)據(jù)的完整性、可靠性無法得到保障。這使得精準(zhǔn)的司法畫像離不開人工的識別與輸入。但即便是對人工而言,發(fā)掘、整理和量化隱含因素也是一項體量浩大且無法精準(zhǔn)把握的工程。其三,由于司法人工智能缺乏主動反思算法缺陷和理解偏差并自我更正的能力,因而其設(shè)計上的缺陷往往需要人工的干預(yù)和糾正,這造成了已不堪重負(fù)的辦案人員還要額外承擔(dān)僵化系統(tǒng)的試錯負(fù)擔(dān)。如在一起盜竊案中,“206 系統(tǒng)”識別出案卷缺少并不需要鑒定的人民幣的鑒定意見,并要求辦案人員作出解釋。辦案人員向?qū)W者抱怨說,“為何系統(tǒng)犯錯卻需要由我來解釋?這就很不合理,此后我再也沒有用過那個系統(tǒng)”[38]。以上這些因素決定了在人工智能的司法應(yīng)用領(lǐng)域“有多少人工才能產(chǎn)出多少智能,有多少優(yōu)秀人工才能產(chǎn)出多少優(yōu)秀智能”的特性,為了保障知識圖譜的準(zhǔn)確性,需要大量的人工通過打標(biāo)簽、選取結(jié)點等方式介入和干預(yù)司法人工智能系統(tǒng)的設(shè)計和應(yīng)用。而這些顯然和人工智能所預(yù)設(shè)的高效性背道而馳。
最后,民眾對司法人工智能決策錯誤率的承受度天然低于人類法官決策。但在人文社科領(lǐng)域,當(dāng)正確率達(dá)到一定程度后,即便少許的提升可能都需要付出無法承受的高昂經(jīng)濟(jì)成本。強(qiáng)魯棒性和高容錯性提升了人工智能在具有一定抽象性和不確定性的司法裁判場景中的預(yù)測性[39]。并且在許多測試中,人工智能已表現(xiàn)出超出人類法官的準(zhǔn)確性。但民眾對于司法人工智能的準(zhǔn)確率要求顯然高于人類法官。其中緣由既有人類本能對新興事物可靠性的擔(dān)憂,也有對人工智能自身缺陷的擔(dān)憂:算法黑箱的存在使發(fā)現(xiàn)和糾正人工智能偏誤的成本極高,且高效、自動化的人工智能應(yīng)用有引發(fā)大規(guī)模錯判的現(xiàn)實風(fēng)險。有學(xué)者指出,“在作為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中,哪怕人工智能僅有 1%的誤差也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人工智能每年可能要處理上百萬件刑事案件,縱使 1%的誤差都有可能造成上萬件冤假錯案。這是民眾所無法接受的”[40]。然而在人文社科領(lǐng)域,希冀達(dá)到 100%的正確率只能是一種鏡花水月的理想,甚至當(dāng)誤差率達(dá)到一定程度后,縱使少量的優(yōu)化也需要付出高昂的經(jīng)濟(jì)成本。故高效和質(zhì)優(yōu)的不可兼得性在一定程度上否決了人工智能完全替代法官裁判的可能性。
三、人工智能時代法官角色轉(zhuǎn)變的前景展望
近年來,人工智能在司法領(lǐng)域的運用已取得豐碩成果。如 2016 年,倫敦大學(xué)學(xué)院、謝菲爾德大學(xué)等高校科研人員研發(fā)的人工智能算法在對歐洲人權(quán)法院 584 個案件的數(shù)據(jù)分析后作出裁決,最終有 79%案件的裁決結(jié)論和法官一致[41]。隨著我國智慧法院建設(shè)的不斷推進(jìn),多地法院也推出了不同版本的智慧審判系統(tǒng),如北京法院的“睿法官”,上海法院的“206 系統(tǒng)”,河北法院的“智審”審判輔助系統(tǒng),等等。然而囿于人工智能與法官裁判的差異性,這些人工智能實際上屬于初級的“簡單案件—法律適用量刑系統(tǒng)”,而不是“復(fù)雜案件—法律推理系統(tǒng)”。雖然根據(jù)訴訟“二八定律”,法院的絕大多數(shù)案件都可以歸為簡單案件[42],并且通過案件自動繁簡分流系統(tǒng)將簡單案件自動分配給人工智能予以裁判④,從而有效地將法官從繁瑣的事務(wù)性、重復(fù)性勞動中解放出來。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主導(dǎo)性地位發(fā)生了動搖,疑難、復(fù)雜、新型案件才是凸顯決策者司法價值和作用的試金石和演武場。基于上文分析,人工智能對于這些案件是無能為力的,只能將其交由人類法官才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裁判結(jié)果。與此同時,人類法官也不能無視人工智能所帶來的變革和挑戰(zhàn),應(yīng)當(dāng)積極轉(zhuǎn)變自身的角色和功能,充分利用“人—機(jī)法律系統(tǒng)”以擴(kuò)展審判能力、提升審判質(zhì)量,從而有效回應(yīng)人工智能時代對法官角色定位的新需求。
(一)更理性化的法官
司法裁判是一項理性化的事業(yè),雖然司法人工智能無法完全替代法官,但司法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承擔(dān)重復(fù)性、事務(wù)性工作以及裁決簡單案件的方式,幫助法官節(jié)省大量精力以投入到疑難、復(fù)雜等案件的事實認(rèn)定、法律適用等裁判的核心工作之中。不僅如此,司法人工智能還能夠通過為法官提供全面的參考數(shù)據(jù)以及簡單的裁判預(yù)測等,避免法官受到價值偏見和知識結(jié)構(gòu)偏差的影響,作出不合理甚至錯誤的裁判。因而,我們應(yīng)當(dāng)充分發(fā)揮司法人工智能在提升法官決策理性化水平中的作用,從而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裁判正義的實現(xiàn)打下良好基礎(chǔ)。
其一,法官應(yīng)當(dāng)充分利用司法人工智能在知識儲備和檢索上的優(yōu)勢,充分占有和發(fā)掘與裁判案件相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先例中的裁判經(jīng)驗,從而降低司法裁判的不確定性,提升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可接受性。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和算力的優(yōu)勢,法官原有認(rèn)知的有限性和模糊性將大為改觀。當(dāng)法官將案件相關(guān)要素輸入系統(tǒng)后,人工智能可通過全量數(shù)據(jù)檢索的方式,自動推送相關(guān)的法律規(guī)定以及類似案例,有效擴(kuò)展法官對案件認(rèn)識的廣度和深度,幫助法官成為一個“開明和信息充分的人”[43],避免片面占有數(shù)據(jù)信息的法官作出缺乏可預(yù)測性的裁判。
其二,無論是先例的推送還是人工智能的裁判預(yù)測,都為法官提供了一種先在決策方案,這使法官需要轉(zhuǎn)變原有“決策—論證”的裁判思維模式,回歸到“論證—決策”這一更具正當(dāng)性的決策框架和范式上來。正當(dāng)?shù)牟门袘?yīng)當(dāng)是法官通過雙方當(dāng)事人提供的證據(jù)、展開的辯論,結(jié)合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定推導(dǎo)出相應(yīng)的裁判結(jié)果。而現(xiàn)實中,法官往往首先憑借對案情的大致了解得出一個模糊的裁判結(jié)論,然后再圍繞這一裁判結(jié)論展開一系列的司法審判活動。受信念固著[44]和錨定效應(yīng)[45]的影響,這種先入為主的論證方式會使法官脫離本應(yīng)當(dāng)秉持的客觀、中立立場。而司法人工智能則通過先例推送和裁判結(jié)果預(yù)測等方式,率先作出了可供法官參照和辯駁的裁判結(jié)論。如在上海法院,若法官的判決結(jié)果和上級法院裁判結(jié)果之間存在的差異達(dá)到 85%以上,其所應(yīng)用的“206 系統(tǒng)”便會向法官發(fā)出預(yù)警。而當(dāng)法官要堅持這一裁判時,系統(tǒng)會自動將此案推送給庭長以供討論[46]。這樣從根本上變革了法官原有的基于對案件模糊印象的直覺而得出裁判結(jié)論的審判思維模式,消除了法官原有證實性偏見的前提和基礎(chǔ)。與此同時,法官還需要努力論證先例裁判結(jié)論或者機(jī)器預(yù)測結(jié)果這一人工智能提供的“它者方案”,從而最大限度削弱了法官的直覺偏見對公正裁判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其三,在利用人工智能輔助裁判的同時,還應(yīng)當(dāng)防范法官過度依賴司法人工智能決策而被“馴服”的風(fēng)險。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限于司法人工智能本身的缺陷,其無法完全替代法官展開司法決策。然而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卻可能出現(xiàn)法官為了避免風(fēng)險、減輕斷案壓力主動交出司法裁判的決策權(quán),從而被人工智能“馴服”,成為司法人工智能的“助手”。為避免此種風(fēng)險的產(chǎn)生,可以通過合理分配司法責(zé)任的方式調(diào)動法官自主裁判的積極性。雖然關(guān)于人工智能在司法領(lǐng)域的責(zé)任歸屬問題存在諸多爭議,但在明確了法官和人工智能的主次定位之后,將錯判或誤判的主要責(zé)任分配給法官,將次要責(zé)任分配給算法提供者或法院將是一種更具可行性和合理性的責(zé)任分配方案。當(dāng)將主要責(zé)任分配給法官之后,法官自然會主動發(fā)揮自身理性,在人工智能力所不能及之處獨立自主、勤勉謹(jǐn)慎地展開司法活動,以保障裁判結(jié)果的正當(dāng)性。
(二)更溫情化的法官
哲學(xué)家維科依照歷史進(jìn)度將司法裁判分為三個階段即神的裁判、常規(guī)裁判、人道的裁判。在這一裁判演化的過程之中,神性因素逐漸隱退,人性和情理因素則逐漸凸顯。與缺乏自主性的、無情的、沒有價值意涵的、沒有反思性的以及無法察覺自己會犯錯的人工智能相比[47],人類法官是有溫度的,其作為社會生活的參與者,擁有和社會大眾一致的共情能力,所致力于實現(xiàn)的也是一種同理心正義。在人工智能對司法裁判全面滲透的背景下,我們所擔(dān)憂的并不是“機(jī)器開始像人類那樣思考,而是人類開始喪失自身獨特的思考能力,成為機(jī)器的附庸” “每個人和每個案例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種都需要人類的判斷力,以及人工智能系統(tǒng)無法提供的、至關(guān)重要而又非常自然的移情能力”[48]。尤其在面對價值沖突、倫理挑戰(zhàn)、階層對立等具有爭議性和隱喻性的案件時,往往需要法官充分運用個體的良知、正義感和同情心展開境遇想象和情感互融,從而體現(xiàn)司法的溫度,避免司法的溫情正義被冷冰冰的機(jī)械正義所取代。
如在著名的柏林守墻士兵亨里奇射殺翻墻青年案中,針對辯護(hù)律師指出的其只是在執(zhí)行命令,因而其是無罪的辯解,審理法官賽德爾指出,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法律命令之外,還有良知,當(dāng)二者發(fā)生沖突時,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應(yīng)當(dāng)主動承擔(dān)良心義務(wù),而不是機(jī)械地執(zhí)行法律。最終亨里奇被判有罪。又如在宜興冷凍胚胎案的二審判決中,法官從倫理、情感和特殊利益保護(hù)的角度指出,“‘失獨’之痛,非常人所能體味。„„涉案胚胎由雙方父母監(jiān)管和處置,既合乎人倫,亦可適度減輕其喪子失女之痛楚”⑤,從而認(rèn)定雙方父母對胚胎的監(jiān)管和處置權(quán)。可以看到,對于這些疑難、新型案件的處理,法官的良心無疑決定了最終裁決的正當(dāng)性和可接受性,這些發(fā)掘法律背后所蘊(yùn)含的良知和正義理念的能力是司法人工智能難以模擬和取代的。從社會生活中汲取經(jīng)驗和智慧,充分將個案置于社會生活背景中予以考量是人類法官獲得民眾信任和認(rèn)可的基礎(chǔ)性條件,真正動人的是鮮活的事實和暖暖的人情味,也正是對人類有溫度的正義需求的積極回應(yīng),司法職能逐漸繁榮并被堅持下來[49]。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更應(yīng)當(dāng)充分發(fā)揮人類法官裁判的獨特價值,努力確證和維護(hù)為社會所共同希冀的倫理秩序、美好情感,充分關(guān)照人類自身的尊嚴(yán)和價值。
(三)更精英化的法官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不斷優(yōu)化及其在司法領(lǐng)域應(yīng)用的不斷擴(kuò)展,法官可以從大量的簡單案件和重復(fù)、機(jī)械的事務(wù)性工作中脫離出來,專心處理少數(shù)疑難、復(fù)雜、新型案件。需要法官處理案件的數(shù)量減少意味著法官人數(shù)需求的下降,但這些少數(shù)疑難、復(fù)雜、新型案件對法官個體的審判素質(zh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意味著少而將精成為今后法官群體的發(fā)展方向。
當(dāng)前,司法改革對推進(jìn)法官精英化具有積極意義。首先,員額制改革通過入額遴選以及提升待遇等方式,既保障了審案法官整體業(yè)務(wù)素養(yǎng),也提升了法官的自我認(rèn)同感。其次,隨著員額制的開展,法官招錄制度也進(jìn)行了相應(yīng)改革。通過招考進(jìn)入法院的人員,往往需要從法官助理干起,經(jīng)過一定年限的實踐培養(yǎng)之后才可獨立審判案件。此外,司法考試改革將接受過法學(xué)專業(yè)的本科或研究生教育作為報考條件,一定程度上通過事先過濾的方式優(yōu)化了法官群體的專業(yè)素養(yǎng)。最后,法官責(zé)任制改革以及人工智能管理系統(tǒng)的引入,使司法活動更加公開化,法官管理制度更加科學(xué)化。法官不得不主動提升自身素養(yǎng),更加謹(jǐn)慎、理性地展開司法活動[50]。這些改革方案推動了法官職業(yè)化、專業(yè)化建設(shè),有效回應(yīng)了人工智能社會對精英法官的需求。但是,這些改革方案對在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司法審判背景下的復(fù)合型法官培養(yǎng)的重視程度還有所不足。
人工智能時代,精英化的法官除了擁有扎實的專業(yè)知識、豐富的審判實踐經(jīng)驗、正直無私的個人品質(zhì)之外,人工智能相關(guān)知識和技能的掌握也應(yīng)當(dāng)成為法官綜合素質(zhì)培育的重要方面。當(dāng)前,由于法律群體對人工智能知識和技術(shù)的生疏,使得司法人工智能系統(tǒng)的建設(shè)往往通過外包的方式展開。在算法黑箱和技術(shù)壁壘的作用下,司法人工智能系統(tǒng)的公正性無法得到保障,且外行制作的司法人工智能時常無法切中司法的真實需求,影響了人工智能和司法審判深度融合的進(jìn)程。積極培養(yǎng)既掌握法律專業(yè)知識也懂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法官,一方面可以保障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主導(dǎo)性地位,避免法官盲目信賴人工智能決策,提升法官運用人工智能法律系統(tǒng)輔助展開裁判的效率;另一方面,懂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法官可以參與到人工智能法律系統(tǒng)的制作、修正等工作之中,也能對算法的公正性展開監(jiān)督,及時發(fā)現(xiàn)人工智能算法所存在的問題,從而有效避免算法黑箱、算法霸權(quán)以及算法歧視等技術(shù)風(fēng)險。
面對我國復(fù)合型人才,尤其是懂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法律人才匱乏的現(xiàn)狀,短期內(nèi)我們可以通過加強(qiáng)法官的培訓(xùn)工作,提升法官對人工智能法律系統(tǒng)的認(rèn)知、了解和操作能力以緩解這一困境。長遠(yuǎn)來看,通過改革現(xiàn)有法律人才培養(yǎng)模式,打造人工智能本科教育加法學(xué)知識研究生教育,或者設(shè)立人工智能、法律交叉學(xué)科并延長培養(yǎng)年限的教育模式是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復(fù)合型法律人才匱乏困境,提升法官精英化水平的可行路徑。當(dāng)前,我國已經(jīng)有一些高校探索開展人工智能法學(xué)的本科與研究生教育,隨著人工智能的深度發(fā)展,需要有更多的高校將培養(yǎng)重心轉(zhuǎn)移到此方面來,以為我國培育更多具有交叉學(xué)科背景的精英化法官提供充足的人才儲備。
四、結(jié)語
面對人工智能時代對法官職業(yè)帶來的挑戰(zhàn),我們既不能冷漠無視,也不必過度焦慮。分析司法人工智能的可能空間與內(nèi)在限度,可以發(fā)現(xiàn),雖然相較于人類法官,人工智能經(jīng)驗更加豐富、立場更加客觀、運轉(zhuǎn)更加高效,但其數(shù)據(jù)化的經(jīng)驗形式、孤立化的裁判立場以及無法兼顧高效和質(zhì)優(yōu)的特性決定了人工智能完全替代法官展開裁判僅僅是一種鏡花水月的理想。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人工智能給法官職業(yè)所帶來的變革性影響。面對正在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法官在借助人工智能輔助提升司法裁判公正性的同時,還應(yīng)當(dāng)努力適應(yīng)人工智能時代法官角色轉(zhuǎn)變的現(xiàn)實需求,成為更加理性化、溫情化和精英化的法官。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